在那杂粮店吃饱喝足后,他们几个坐在那里聊,我转身上街进行“社会调查”了。看路边有个三轮电动摩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头伸出来在张望,我凑上前去递上一根烟便聊开了。
渭北的“黑腰带”从铜川西开始到这里已接近“腰带头”了。澄县的支柱产业是煤,是澄合矿务局机关所在地。看着那路边的子弟小学和中学以及医院、俱乐部就知道在那个公有制年代的红火。但如今已经是一幅颓败相了。原因:一是本身这里的煤含硫量就比较高,加之大规模的开采已经接近枯竭了。二是煤矿改制,工人下岗分流“自谋生路”了。至于种地农村如今已“十室九空”了,地能包出去就包了,包不出去就荒了,他曾经算过一笔账,一亩地的麦子辛苦半年下来的利润是30.54元(还没有除去劳动力的付出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你来了还会去种地吗?所以现在再搞人口普查的话,也只能按户籍所在地那个本本上统计了,实际的人都天南海北,到过大年也才能回来一半。这种现象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是难免的,并且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就这样我和他互动了大约二十多分钟,受益大啊!我到一个地方就爱找老头和街上开出租的人聊,他们对当地的情况熟悉。书本上的东西有些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社会变化太快了,仅靠“老黄历”来判断,那我这个“侦察参谋”也就不称职了。
上车继续北行。农田和村落不断的从车窗边滑过,在泾三高地区麦浪滚滚的喜人景象在这里已看不见了,看见的是那出土才不到二十公分的地膜玉米和那绿色的苹果园。澄县到黄龙是七十二公里,大约走有二十多公里就接近北山了,在山底下有座古镇----冯塬。这可以说是渭北台塬沟壑地形的最后一个镇了。镇子还是蛮大的,有些老民居。渭北这个地区的窑洞和陕甘宁边以及陕北高原上的窑洞不太一样。这里的窑洞是在平地上用模板搭架子,箍上砖后就往那上面填土再夯实。而陕甘宁边区的窑洞都是用最原始的方式在山坡上硬掏的。陕北米绥地区的窑洞圈窑的方式上和这里相同,但大多都是依山势上下相叠而修建的。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我想:一是地质构造和土质决定的。二聚落是根据土地的分布、地形、水源、劳作方式、交通等因素来决定是聚集还是散落。窑洞本身就是干燥和极端气候的产物,当然还有财力的因素了。
我发现渭北的村落都比较大而集中。整体布局是窑洞的前面是院子,背后是街道。无窗户,保暖、防风,很像是个大的防御工事(和福建永定客家人的土楼有点相似)。好似那东非大草原上的斑马群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都聚成个圈,屁股一律朝外,以蹄代拳。渭北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匪多,匪也是依托山区生存的,手段多是奔袭作案。活动半径都是在五十到七十里之间,抢、绑完后迅速撤离到山里去了。出没无常,让政府十分头疼,于是村落自保就成为主要手段了。看来就一个窑洞村落的设计上还包含着治安因素。
这里的人性情还是比较平和。不像那“一说二骂三动拳”的渭北平原地区的人那样刁蛮、凶悍。陕西有句民谚“刁蒲城,野渭南,不讲理的大荔县”,一个地方民风的形成一定是有它的历史原因。那里比较富庶,又是交通要道,兵匪抢掠,豪强敲诈,如果人要是都和绵羊似的生存就困难了。土匪讲理还叫土匪吗?也只能以强悍对强悍了。那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爱国将领之一蒲城籍杨将军虎城就是刀客出身,那也是当时半殖半封中国社会的产物了。当然,那已经是历史了如今很少见了,民风也不是一尘不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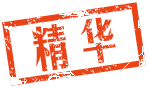
 /1
/1 